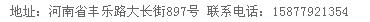周梦蝶:本名周起述,年2月6日(年腊月二十九)-年5月1日下午2点48分病逝,享寿94岁。河南籍台湾著名诗人,为台湾国家文学奖首位获得者。出生于河南淅川。原就学于开封师范、宛西乡村师范,由于家境及战乱肄业。年去武汉求学未成,生活无着投军,后随军撤到台湾。年开始发表诗作,加入蓝星诗社,年4月自费出版诗集《孤独国》,销路不佳。年7月出版诗集《还魂草》,受到诗坛瞩目。周梦蝶是诗坛少有的蜗牛派,创作半个世纪,却字字珍惜,至今只出版过五部诗集《孤独国》、《还魂草》、《十三朵白菊花》、《约会》和《有一种鸟或人》(大陆仅正式出版过一部诗选集《刹那》)。他的生命全献给了诗,诗和他的生命已分不开,而这颗未蒙尘的珍珠,也实至名归地获得第一届“国家文艺奖”。
十月
就像死亡那样肯定而真实你躺在这里。十字架上漆着和相思一般苍白的月色而蒙面人的马蹄声已远了这个专以盗梦为活的神窃他的脸是永远没有褶纹的风尘和抑郁折磨我的眉发我猛叩着额角。想着这是十月。所有美好的都已美好过了甚至夜夜来吊唁的蝶梦也冷了是的,至少你还有虚无留存你说。至少你已懂得什么是什么了是的,没有一种笑是铁打的甚至眼泪也不是……
树
等光与影都成为果子时,你便怦然忆起昨日了。那时你的颜貌比元夜还典丽,雨雪不来,啄木鸟不来,甚至连一丝无聊时可以折磨自己的触须般的烦恼也没有。是火?还是什么驱使你冲破这地层?冷而硬的,你听见不,你血管中循环着的呐喊?“让我是一片叶吧!让霜染红,让流水轻轻行过……”于是一觉醒来便苍翠一片了!雪飞之夜,你便听见冷冷青鸟之鼓翼声。
逍遥游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庄子
绝尘而逸。回眸处乱云翻白,波涛千起;无边与苍茫与空旷展笑着如回响遗落于我踪影底有无中。从冷冷的北溟来我底长背与长爪犹滞留着昨夜的濡湿;梦终有醒时——阴霾拨开,是百尺雷啸。昨日已沉陷了,甚至鲛人底雪泪也滴干了;飞跃呵,我心在高寒高寒是大化底眼神我是那眼神没遮拦的一瞬。不是追寻,必须追寻不是超越,必须超越云倦了,有风扶着风倦了,有海托着海倦了呢?堤倦了呢?以飞为归止的仍须归止于飞。世界在我翅上一如历历星河之在我胆边浩浩天籁之在我肋下……
菩提树下
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谁肯赤着脚踏过他的一生?所有的眼都给眼蒙住了谁能于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在菩提树下。一个只有半个面孔的人抬眼向天,以叹息回答那欲自高处沉沉俯向他的蔚兰。是的,这儿已经有人坐过!草色凝碧。纵使在冬季纵使结跗者的足音已远去你依然有枕着万籁与风月的背面相对密谈的欣喜坐断了几个春天?又坐熟了几个夏天?当你来时雪是雪,你是你一宿之后雪即非雪,你亦非你直到零下十度的今夜当第一颗流星暗然重明你乃惊见:雪还是雪,你还是你虽然结跗者的足音已远去唯草色的凝碧
燃灯人
因果经云:「尔时善慧童子见地浊湿,即脱鹿皮衣,散发匍匐,待佛行过。」又云:「过去帝释化为罗剎,为释迦说半偈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释迦请为说全偈。渠言:『我以人为食,尔能以身食我,当为汝说。』释迦许之。渠乃复言:『生灭灭已,寂灭为乐。』释迦闻竟,即攀高树,自投于地。」走在我底发上。燃灯人宛如芰荷走在清圆的水面上浩瀚的喜悦激跃且静默我面对泥香与乳香混凝的夜我窥见背上的天溅着眼泪曾为半偈而日食一麦一曾为全偈而将肝脑弃舍在苦行林中,任鸟雀在我发间筑巢任枯叶打肩,霜风洗耳灭尽还苏时,坐边扑满沉沉的劫灰隐约有一道暖流幽幽地流过我底渴待。燃灯人,当你手摩我顶静似奔雷,一只蝴蝶正为我预言一个石头也会开花的世纪当石头开花时,燃灯人我将感念此日,感念你我是如此孤露、怯羞而又一无所有除了这泥香与乳香混凝的夜这长发。叩答你底弘慈曾经我是腼腆的手持五莲花的童子
垂钓者
是谁?是谁使荷叶,使荇藻与绿萍,频频摇动?揽十方无边风雨于一钓丝!执竿不顾。那人由深林第一声莺,坐到落日衔半规。坐到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之背与肩被落花压弯,打湿……有蜻蜓竖在他的头上,有睡影如僧定在他垂垂的眼皮上,多少个长梦短梦短短梦,都悠悠随长波短波短短波以俱逝——-在芦花浅水之东醒来时。鱼竿已不见,为受风吹?或为巨鳞衔去?四顾苍茫,轻烟外,隐隐有星子失足跌落水声,铿然!
九行
你底影子是弓你以自己拉响自己拉得很满,很满。每天有太阳从东方摇落一颗颗金红的秋之完成于你风干了的手中。为什么不生出千手千眼来?既然你有很多很多秋天很多很多等待摇落的自己。
摆渡船上
负载着那么多那么多的鞋子船啊,负载着那么多那么多相向和背向的三角形的梦。摇荡着——深深地流动着——隐隐地人在船上,船在水上,水在无尽上无尽在,无尽在我刹那生灭的悲喜上。是水负载着船和我行走?抑是我行走,负载着船和水?暝色撩人爱因斯坦底笑很玄,很苍凉。
二月
这故事是早已早己发生了的在未有眼睛以前就已先有了泪就已先有了感激就已先有了展示泪与感激的二月而你眼中的二月何以比别人独多?总是这样寒澹澹的天色总是这样风丝丝雨丝丝的——降株草底眼睫垂得更低了绎殊草底服睫垂得更低了“怎样沁人心脾的记忆啊那自无名的方向来饮我以无名的颤栗的……”而你就拼着把一生支付给二月了二月老时,你就消隐自己在星里露里。
六月
枕着不是自己的自己听听隐约在自己之外而又分明在自己之内的那六月的潮声从不曾冷过的冷处冷起千年的河床,瑟缩着从臃肿的呵欠里走出来把一朵苦笑如雪泪撒在又瘦又黑的一株玫瑰刺上霜降第一夜。葡萄与葡萄藤在相逢而不相识的星光下做梦梦见麦子在石田里开花了梦见枯树们团团歌舞着,围着火梦见天国象一口小麻袋而耶稣,并非最后一个肯为他人补鞋的人
托钵者
滴涓涓的流霞于你钵中。无根的脚印啊!十字花开在你匆匆的路上衣明囚与昨日与今日之外你把忧愁埋藏。紫丁香与紫苜蓿念珠似的到处牵接着你;日月是双灯,袈裟般夜的面容。十四月。雪花飞三千弱水的浪涛都入睡了。向最下的下游——最上的上游问路。问路从几时有?几时路与天齐?问忧昙华几时开?隔着烟缘,隔着重重的流转与流转——你可能窥见哪一粒泡沫是你的名字?长年辗转在恒河上恒河的每一片风雨每一滴鸥鹭都眷顾你——回去是不可能了。枕着雪涛你说:“我已走得太远!”所有的渡口都有雾锁着在十四月。在桃叶与桃叶之外抚着空钵。想今夜天上有否一颗陨星为你默默堕泪?象花雨,象伸自彼岸的圣者的手指……附:优昙华三千年一度开,开必于佛出世日。又:王献之有妾曰桃叶,美甚,献之尝临流歌以送之。后遂以桃叶名此渡。
·让让软香轻红嫁与春水让蝴蝶死吻夏日最后一瓣玫瑰,让秋菊之冷艳与清愁酌满诗人咄咄之空杯;让风雪归我,孤寂归我如果我必须冥灭,或发光──我宁愿为圣坛一蕊烛花或遥夜盈盈一闪星泪。·索是谁在古老的虚无里撒下第一把情种?从此,这本来是只有“冥漠的绝对”的地壳便给鹃鸟的红泪爬满了。想起无数无数的罗蜜欧与朱丽叶想起十字架上血淋淋的耶稣想起给无常扭断了的一切微笑……我欲抟所有有情为一大浑沌索曼陀罗花浩瀚的瞑默,向无始!·祷帝呀!我求你借给我你智慧的尖刀!让我把自己──把我的骨,我的肉,我的心……分分寸寸地断割分赠给人间所有我爱和爱我的。不,我永无吝惜,悔怨──这些本来都不是我的!这些本来都是你为爱而酿造的!──现在是该我“行动”的时候了,我是一瓶渴欲流入每颗靦腆地私语着期待的心儿里的樱汁。·云永远是这样无可奈何地悬浮著,我的忧郁是人们所不懂的。羡我舒卷之自如么?我却缠裹着既不得不解脱而又解脱不得的紫色的镣铐;满怀曾经沧海掬不尽的忧患,满眼恨不能沾匀众生苦渴的如血的泪雨,多少踏破智慧之海空不曾拾得半个贝壳的渔人的梦,多少愈往高处远处扑寻而青鸟的影迹却更高更远的猎人的梦,尤其,我没有家,没有母亲我不知道我昨日的根托生在那里而明天──最后的今天──我又将向何处沉埋……我的忧郁是人们所不懂的!羡我舒卷之自如么?·雾从一枕黑甜的沉溺里跳出来,湿冷劈头与我撞个满怀──回教女郎的面纱深深掩罩着大地,冥蒙里依稀可闻蜗牛的喘息;夸父哭了,羲和的鞭子泥醉着眈眈的后羿的虹弓也愀然黯了颜色;而向日葵依旧在凝神翘望,向东方!看有否金色的车尘自扶桑树顶闪闪涌起;小草欠伸著,惺忪的睫毛包孕著笑意:它在寻味刚由那儿过来的觭幻的梦境它梦见它在葡萄酒色的紫色海里吞吐驰骤它是一头寡独、奇谲而桀骜的神鲸……当阳光如金蝴蝶纷纷扑上我襟袖,若不是我湿冷褴褛的影子浇醒我我几乎以为我就是盘古第一次拨开浑沌的眼睛。·有赠我的心忍不住要挂牵你──你,危立于冷冻里的红梅!为什么?你这般迟迟洩漏你的美?你把你艳如雪霜的影子抱得好死!梅农的雕像轻轻吟唱着,北极星的微笑给米修士盗走了……雪花怒开,严寒如喜鹊窜入你襟袂噫,你枕上沉思的缪司醒未?·徘徊一切都将成为灰烬,而灰烬又孕育著一切──樱桃红了,芭蕉忧郁著。他不容许你长远的红呢!他不容许你长远的忧郁呢!“上帝呀,无名的精灵呀!那么容许我永远不红不好么?”然而樱桃依然红着,芭蕉依然忧郁著,──第几次呢?我在红与忧郁之间徘徊著。·除夕一九五八年,我的影子,我的前妻投了我长长的恻酸的一瞥,瞑目去了……但愿“新人”不再重描伊的旧鞋样!她该有她自己的──无帮儿无底儿的;而且,行动起来虽不一定要步步飏起香尘──你总不能教波特莱尔的狗的主人 绝望地再哭第二次·又踅过去了又踅过去了!连瞥一眼我都没有;我只隐隐约约听得他那种踌躇满志幽独而坚冷的脚步声。“已没有一分一寸的余暇容许你挪动‘等待’了!你将走向哪里去呢?成熟?腐灭?”这声音沉默地撞击着我如雪浪我边打着寒噤,边问自己:我究曾让他蚕蚀了我生命多少!?慈仁而又冷酷慷慨而又悭吝……他是我的挛生兄弟呢。·寂寞寂寞蹑手蹑脚地尾着黄昏悄悄打我背后里来,裹来缺月孤悬天中又返照于荇藻交横的溪底溪面如镜晶澈只偶尔有几瓣白云冉冉几点飞鸟轻噪著渡影掠水过……·我趺坐著看了看岸上的我自己再看看投映在水里的醒然一笑把一根断枯的柳枝在没一丝破绽的水面上著意点画著“人”字──一个,两个,三个……·冬至流浪得太久太久了,琴,剑和贞洁都沾满尘沙。鸦背上的黄昏愈冷愈沉重了,怎么还不出来?烛照我归路的孤星洁月!一叶血的遗书自枫树指梢滑坠,荒原上造化小儿正以野火燎秋风的虎须……“最后”快烧上你的眉头了!回去回去,小心守护它;你的影子是你的。·乌鸦哽咽而怆恻,时间的乌鸦呜号著:“人啊,聪明而蠢愚的啊!我死去了,你悼恋我;当我偎依在你身旁时,却又不睬理我──你的瞳彩晶灿如月镜,唉,却是盲黑的!盲黑得更甚于我的断尾……”时间的乌鸦呜号著,哽咽而怆恻!我搂著死亡在世界末夜跳忏悔舞的盲黑的心刹那间,给斑斑啄红了。·晚虹当晚虹倩笑著以盛妆如新嫁娘的仪采出现的时候──一身血一身汗一身泥的劳人,以为它是一张神弓想搭在它的弓弦上如一只箭轻飘飘地投射到天堂的清凉里去;给太多的空闲绞得面色惨青可怜的上帝!常常悄悄悄悄地从天堂的楼口溜下来在它绚灿的光影背后小立片刻──只为一看太阳下班时暖红的笑脸,只为一嗅下界飞沙与烟火氤氲的香气,只为一吻顶满天醉云归去的农女的斗笠和一听特别快车趋近解脱边缘时洒落的尖笑……·乘除一株草顶一颗露珠一瓣花分一片阳光聪明的,记否一年只有一次春天?草冻、霜枯、花冥、月谢每一胎圆好里总有缺陷孪生寄藏!上帝给兀鹰以铁翼、锐爪、钩、深目给常春藤以嬝娜、缠绵与执拗给太阳一盏无尽灯给蝇蛆蚤虱以绳绳的接力者给山磊落、云奥奇、雷刚果、蝴蝶温馨与哀愁……·默契生命──所有的,都在觅寻自己觅寻已失落,或掘发点醒更多的自己……每一闪蝴蝶都是罗蜜欧痴爱的化身,而每一朵花无非朱丽叶哀艳的投影;当二者一旦猝然地相遇,便醉梦般浓得化不开地投入你和我,我和你。而当兀鹰瞩视著纵横叱吒的风暴时当白雷克于千万亿粒沙里游览著千万亿新世界当惠特曼在每一叶露草上吟读著爱与神奇当世尊指间的曼陀罗照亮迦叶尊者的微笑当北极星枕著寂寞,石头说他们也常常梦见我……·错失十字架上耶稣的泪血凝冻了,我理智的金刚宝剑犹沉沉地在打盹;谁说人是最最灵慧而强毅的?竟抗抵不了“媚惑”甜软的缠陷的眼睛。你说,也许有一天你会怀孕(你将炼铸一串串晶莹丰圆的紫葡萄出来)是的,也许有一天荆棘会开花而一夜之间,维纳丝的瞎眼亮了……谁晓得!上帝会怎样想?万一真真有那么一天,很不幸的我担忧著:我仿佛烛见
一座深深深深锁埋著的生之墓门面对著它,错失哭了;
握在真理手中的钥匙也哭了。·菱角偎抱著十二月的严寒与酷热你们睡得好稳、好甜啊你们,这群爱做白日梦的你们,翅膀尖上永远挂著微笑的一只只手的贪婪,将抓走多少天真?热雾袅绕,这儿正有人在蒸煮、贩买蝙蝠的尸体!一袭袭铁的紫絮外套,被斩落一双双黑天使的翅膀,被斩落一瓣瓣白日梦,一弯弯笑影……上帝啊,你曾否赋予达尔文以眼泪?·孤独国昨夜,我又梦见我赤裸裸地趺坐在负雪的山峰上。这里的气候黏在冬天与春天的接口处(这里的雪是温柔如天鹅绒的)这里没有嬲骚的市声只有时间嚼著时间的反刍的微响这里没有眼镜蛇、猫头鹰与人面兽只有曼陀罗花、橄榄树和玉蝴蝶这里没有文字、经纬、千手千眼佛触处是一团浑浑莽莽沉默的吞吐的力这里白昼幽阒窈窕如夜夜比白昼更绮丽、丰实、光灿而这里的寒冷如酒,封藏著诗和美甚至虚空也懂手谈,邀来满天忘言的繁星……过去伫足不去,未来不来我是“现在”的臣仆,也是帝皇。·在路上这条路好短,而又好长啊我已不止一次地走了不知多少千千万万年了黑色的尘土覆埋我,而又粥粥鞠养著我我用泪铸成我的笑又将笑洒在路旁的荆刺上会不会奇迹地孕结出兰瓣一两蕊?迢遥的地平线沉睡著这条路是一串永远数不完的又甜又涩的念珠·行者日记昨日啊曾给罗亭、哈姆雷特底幽灵浸透了的湿漉漉的昨日啊!去吧,去吧我以满钵冷冷的悲悯为你们送行我是沙漠与骆驼底化身我袒卧著,让寂寞以无极远无穷高负抱我;让我底跫音沉默地开黑花于我底胸脯上黑花追踪我,以微笑底忧郁未来诱引我,以空白底神秘空白无尽,我底忧郁亦无尽……天黑了!死亡斟给我一杯葡萄酒我在峨默疯狂而清醒的瞳孔里照见永恒,照见隐在永恒背后我底名姓
峨默·开阳(OmarKhayyam),波斯诗人,“鲁拜集”作者,有“遗身愿裹葡萄叶,死化寒灰带酒香”之句。·第一班车乘坐著平地一声雷朝款摆在无尽远处的地平线无可奈何的美丽,不可抗拒的吸引进发。三百六十五个二十四小时,好长的夜!我的灵感的猎犬给囚锢得浑身痒痒的渴热得像触嗅到火药的烈酒的亚力山大。大地蛰睡著,太阳宿醉未醒看物色空蒙,风影绰约掠窗而过我有踏破洪荒、顾盼无俦恐龙的喜悦。而我的轨迹,与我的跫音一般幽敻寥独我无暇返顾,也不需要休歇狂想、寂寞,是我唯一的裹粮、喝采!不,也许那比我起得更早的启明星,会以超特的友爱的